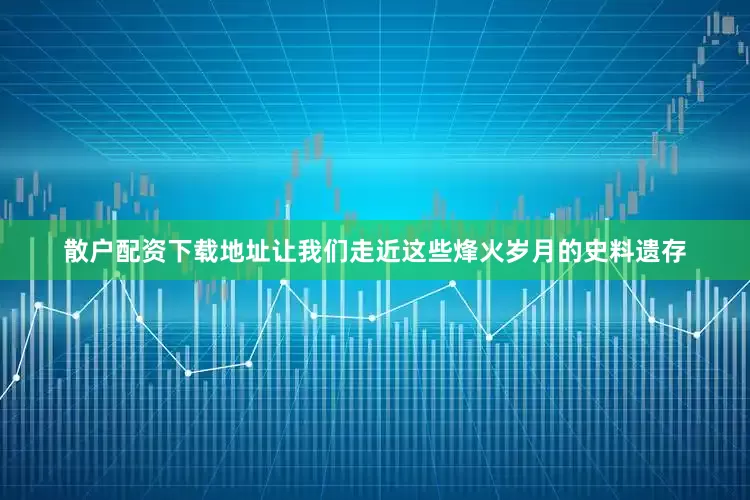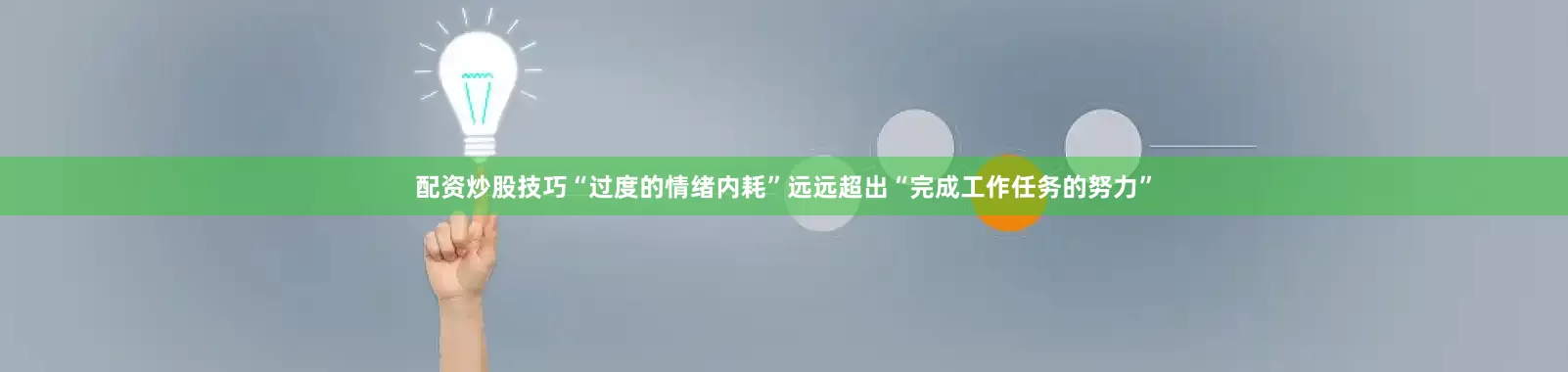
据《工人日报》报道,本是集中在服务行业的情绪劳动,如今在不同行业有泛化趋势。随着工作中“线上情绪输出”场景的增多,不少劳动者感叹,“过度的情绪内耗”远远超出“完成工作任务的努力”,这也使得情绪劳动这一“老概念”得到了“新关注”。什么是情绪劳动?为什么很多人会被情绪劳动所困?劳动者该如何调节?本期我们一起来听听老大哥们怎么说。
职场人应适当给自己减减压
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岑凡:情绪劳动大多是指为了让组织、他人感到满意和舒适而调节自己的情绪和表情所付出的、常常被忽视的劳动。很多人可能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,在贵州毕节一个高速收费站内,一名女收费员在站内用双手抹眼泪,表情委屈,但是有车辆路过时,收费员立刻控制住情绪,转头微笑面对顾客进行服务,回过头来才又用衣袖抹了抹眼泪。她的含泪微笑服务就是标准的情绪劳动。
各行各业都要跟人打交道,态度、心情、心态是双方交流顺畅不可或缺的因素。企业要提高工作成效,就一定会要求员工在服务客户、与客户打交道中,注意情绪,尽可能让人感到愉悦、舒畅。这时候,劳动者是作为一个职场人被要求,而个人的真实情绪、心理感受则被要求隐藏甚至扭曲。说到底,成年人的职场没有容易二字,也不可能随心所欲。
情绪劳动同样要付出心力,甚至比体力劳动更加让人“疲惫”,谁经历,谁知道。长期“动心忍性”,不免给劳动者身心带来不利影响,让精神处于“亚健康”状态,甚至出现忧郁问题。对于劳动者来说,要意识到这个问题,适当给自己减压、放松,比如参加体育娱乐活动,跟家人、朋友倾诉等,尽可能消除负面情绪。如果实在承受不了,就别绷紧那根弦了,躺平不干也没事,没有比身心健康更加重要的事情了。对于企业,应看到情绪劳动的价值,理解员工的不容易,工作中可采取轮岗、轮班的方式调节,也可组织各类活动,设置“委屈奖”“情绪假”等给员工解绑、放松。
情绪劳动理应获得合理对价
《浙江工人日报》评论作者王志顺:当下某些企业要求的已不是专业服务应有的情绪管理,而是彻底的情感驯化——银行职员需要帮客户接送孩子、混凝土销售要为客户修图……这些远超工作范畴的要求,本质上是用“顾客至上”的幌子侵占劳动者的情感边疆。更值得警惕的是,随着数字化办公的普及,“线上情绪表演”成为新的重灾区。工作群里的“秒回文化”,汇报时必备的“阳光语气”,甚至离职时都要保持“感恩体面”,使得情绪劳动突破时空界限,演变为24小时待机的精神酷刑。
这种过度的情绪消耗正在制造触目惊心的“情感工伤”。上海咖啡店员工向顾客泼咖啡粉的极端事件,不过是情绪高压锅爆炸的冰山一角。心理学研究表明,当人长期压抑真实感受表演情绪时,大脑边缘系统会持续处于应激状态,最终导致两种后果:要么如西安销售李宇豪般陷入中度抑郁,要么产生“去人格化”的职业病症——医护人员对病痛麻木、教师对学生失去共情,这些本质上都是心理防御机制崩溃的前兆。更隐蔽的危害在于,情绪劳动的不平等分配加剧了职场歧视。女性通常被要求付出更多“亲和力溢价”,年轻人被迫接受“情商PUA”,这些隐形规则正在重塑畸形的职场生态。
在情绪经济价值被无限放大的今天,我们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:劳动者的微笑不该是无限量供应的免费资源。职场中的情绪劳动也应当获得合理对价——无论是物质补偿还是制度保障。毕竟,一个健康的社会,不该让劳动者的心灵长期处于“情感赤字”状态。唯有承认“情绪有价”,才能真正实现霍克希尔德期待的“情感整饰”与“自我真实”的平衡。
从“隐形付出”转变为“有价值的贡献”
《浙江工人日报》评论作者文魁:让情绪劳动有“获得感”,需要制度保障与观念转变协同发力。企业层面可从三方面着手突破:建立量化评估机制,如某连锁酒店专门设置“情绪劳动补贴”,根据服务质量动态调整;完善权益保障制度,像部分航空公司为乘务员推出“心理假”,允许每月申请一天进行情绪调适;借助技术手段减负,例如电商平台引入AI系统自动拦截极端辱骂信息,减少人工直面的情绪冲击。社会层面则需重构对服务行业的认知:当消费者对冒雨送货的快递员说句“辛苦了”,当家长对嗓子沙哑的老师道声“多休息”,当管理者对妥善处理纠纷的下属夸句“做得很棒”,这些细微处的尊重所带来的精神满足,远比物质奖励更能消解情绪劳动的深层疲惫。
就像诚信是商业运行的根基,尊重亦是社会协作的润滑剂。当每一份克制的微笑都能被看见背后的隐忍,每一次耐心的倾听都能被珍视蕴含的付出,每一回得体的应对都能被认可承载的专业,情绪劳动才能真正从“隐形付出”转变为“有价值的贡献”,劳动者才能在日复一日的情绪调控中,持续收获尊严与前行的动力。毕竟,让用心服务的人得到应有的回报,让默默付出的情绪劳动获得应有的重量,才是社会文明最生动的注脚。
地方配资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